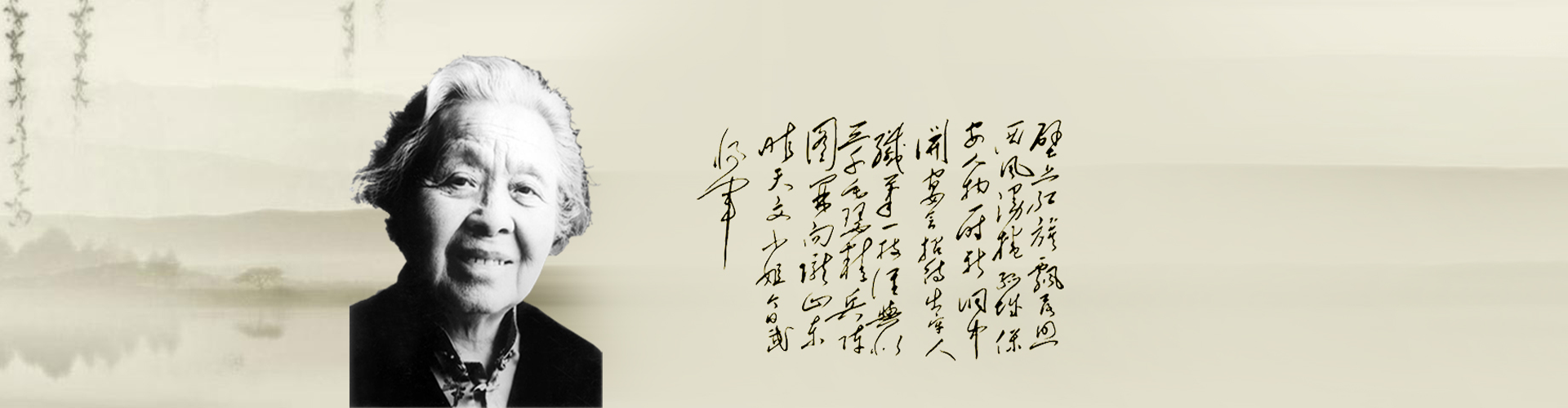2018年第2期 

丁玲的五十年代前后: 从互助合作化运动谈起
[返回]丁玲的五十年代前后:从互助合作化运动谈起
〔台湾〕钟秀梅[1]
土改进行中
根据学者王景新的《中共早期的互助合作运动及其探索》一文指出,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互助合作运动”性质是反帝与反封建性质,中国共产党起了推进的领导作用,“从经济方面说,组织农民合作社,是发展生产,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从军事方面说,组织农民合作社也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2]。”
王教授认为一九二十年代中央苏区所领辖的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人口450万。这些地区受限于宗族势力垄断掌握土地权,地租负荷太高,阻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贫困化人口剧增。另一方面,中央苏区的农业经济体,受制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商品经济受阻,必须寻求另类替代方案的选择[3],合作化运动一途解决了危机,实践了战时社会主义体制的可能性[4]。不论是苏联或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战争时期的性质与时间维系不同,若以井冈山根据地组建时间的1927年到1947年国民党退出历史舞台为止,中国战时社会主义体制维持长达二十年的经验,也奠定往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
合作化运动的基础是土地改革,当时富有想象力的劳动互助合作社组织出现了;第一个犁牛合作社在江西省瑞金武阳区五水乡成立,被认为是“当时根据地出现的一种较劳动互助社更高级的互助合作形式”。其它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保障了根据地军需民用、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兴办的造纸、织布、炼铁、农具、铸锅、石灰、砖瓦、竹木器等生产合作社一一成形。1928年10月,赣西南东固区东固消费合作社(最早的消费合作社)成立。1929年,信用合作社,其它如粮食生产合作社,调节根据地粮食价格,提高生产量,解决中间剥盘的问题[5]。学者应星对于东固根据地的地方干部、红色武装和组织型态有深入研究,应星认为东固根据地是赣西南最早实现的工农武装割据地,因此不难想象东固消费合作社的历史地位[6]。
王景新认为中央苏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包含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与解放区等三个阶段。四十年代上半叶的抗日战争时期经历困难期。在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的变化。耕者有其田制度的实行,使广大的贫雇农得到了土地,激发了他们生产和支持前线的积极性。”[7]
《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作者艾列克·吴尔芙(Eric R.Wolf)对于中国土地改革伴随着新形式的集体组织如村委会、工作小组、农会等,让社会主义新农村注入活力[8]。吴尔芙估计,以村自治组织为单位的合作化运动到了1927年底由原16,000个增加为58,000(成长为三倍多),1933-34年稍微下降至40,000个(长征、苏区撤守),但是到了1947年左右,又增长为1,000,000个[9]。
吴尔芙对于二十世界中国农民战争下了如此定义:“过往农民起义的千年梦成真,成为社会现实,新中国声称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而不是孔圣之志。然而,中国共产党从众多的人口中拔筹与训练统治菁英的传统概念,与科举制通过非血缘世袭与开放的选才过程有一致性。同样地,水利经营与公共事业的伟大传统,提供国家承担决策最初和最终的办法,国家不仅仅是政治整体,也是道德秩序的承担者,在仪式与庆典中表达出来。[10]”吴尔芙观察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国共产革命从农民的集体主义与利他的意识型态得到支持,此道德说服相较于政治或军事力量而言,才是新社会最终的支持,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延续。
丁玲在《在霞村的日子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严寒的日子里》中对于霞村、白槐庄、暖水屯、果园村等以村集体为单位的反抗帝国主义与土地改革运动有详尽的描写,若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纪实小说为主要文本,如何分析与呈现中国合作化运动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历程的能动性?叙事特点为何?
村集体与能动性
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国革命奠立了基底,著名的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将他1948年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蹲点亲历土改的经验所写成的非纪实小说《翻身》(Fanshen)做出判断,他说:“因此战争真是在凶残与无情中成长,双方被决定性的战役包围,妥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每日的发展证明1947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年。”[11]根据韩丁的估计,当年北方根据地支持土地革命的人口高达一亿,其基础在于1947年中共中央所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the Draft Agrarian law),保障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2]。《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分析,1947年前,占全部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全国土地的70%到80%,全国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占全国土地20%到30%[13]。《中国土地法大纲》延续着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并修正《五四指示》的土改的不彻底性[14]。从1946年起笔到1948年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细腻地纪录了革命中的农村之巨变,也见证着韩丁所谓的关键的一年。
一九四十年代的中国,从千年封建蜕变为新社会,是受压迫阶级的关键年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年代或“转折时代”,学者李松睿指出除了上述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之外,作家转向(向左转),介入人民的艺术使然[15]。贺桂梅指出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为界,“共产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社会动员方式上都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不仅因此打破了偏僻乡村中压迫与停滞的循环,解决了日本和国民党政府双重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并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广泛参与抗战活动(人民战争),同时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建国模式的雏形。这一成功的另类实践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延安道路’。”[16]
“延安道路”需从历史性且辩证的角度來理解,马克·赛尔登从国际共产运动与国内阶级翻身的角度肯定延安道路。从世界反体系运动的角度,它体現的了世界边缘地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从国內角度,面对日帝“扫荡”,国共军事摩擦,根据地财政困难等,以群众路线的人民战争,用自立更生的精神,解放了占主要人口的穷人的生活,总结了几十年來根据地时间经验理论化的结果[17]。
“延安道路”中知识份子主体性问题,经常被聚焦放大与去历史脉络(如王泛森),丁玲也经常被对号入座,一般的说法是,整风后的知识份子与作家:“在革命政权內,作家(知识分子)是政权话语的传播者甚至监督者,还是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社会现实状况具有自主阐释的权利,甚至对毛话语本身提出反省或质疑的批判者。亦即,这一问题涉及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权中被给一定的位置,及其可能的活动方式和活动空间。”[18]然而,根据丁玲的访谈:“从过去沒想得这么多,只想到为工农大众写普罗文学,写无产阶级。学习《讲话》后明确认识到,如果不到工农兵中间去,怎么写好工农兵呢?一定要下去,长期在他们中间,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兴趣。”[19]
丁玲所强调的“长期在他们中间,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兴趣”,涉及了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的问题,而批判与自我批判是国际共产运动中,面对外在形式(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暴力)与内在主客体状态的整体(包括社会主义政经成熟度、民主程度、公民与党组织的活动力、政治意识与意识型态的水平等),所涉及广大公众利益的负责任的政治行动[20]。因此,丁玲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21]的文学生产在复杂的国际共产运动与国内的互助合作运动史的脉络下,是批判与自我批判,改造与自我改造的特殊的历史的政治与文学行动。
194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丁玲欢喜若狂,她想她不要再闲在张家口了,这下可以要求参加的战斗了。这样,她的眷恋之情就有了新的寄托。于是,她立要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的土地改革工作队。7月,她被批准参加晋察冀土地改革工作团,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接着就投入怀来、涿鹿一带土改工作。[22]
根据许华斌的访谈,丁玲:“在桑干河畔,走马观花地住过九个村子,最后在涿鹿县温泉屯村里参加一个月的工作。她轮流着吃派饭,走家串户,访贫问苦,整天和男女老少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聊天,甚至晚上还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头聊家常,什么儿子、媳妇啊,什么哪家好、哪家不好啊……不论对什么人,她都不嫌弃他们,不讨厌他们。”[23]丁玲下乡田调中,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秋天她参与土地会议,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冬天她随华北联大土改工作队去束鹿。1948年年初,丁玲到了石家庄近郊的宋村,参加了约四个月时间的土地平分工作。[2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人物表长达36人,有旧社会的成员(地主、佃农、中农、村长、妇女)和参与土地改革组织与份子(工会、宣传部、土改工作组、书记、民兵、合作社、妇联会青联会、乡村教师等)。这部小说对于丁玲文学的文学创作阶段有突破性的成就,丁玲研究专家叶昌前认为:“作为一个在创作中已经走向成熟的作家,丁玲不但在这部长篇中已经找到,已经把握了清隽而深沉的语言风格,并巩固和充实起来,而且体现着她对反映新生活的语言途径的进一步探求。她是朝着语言的大众化道路迈进的,但走的又是带着自己鲜明特点的大众化道路[25]。”
土地改革、分地是这本小说的核心命题。然而,丁玲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形成以辩证的历史唯物论来理解,比如丁玲所描写的中富农顾涌的家族累积财富的历史,非简单的成分划分,居中,丁玲观察到:
他们经过了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被残酷的历史剥蚀着,但他们由于不气馁的勤苦,慢慢的有了些地,而且在土地上抬起头来了。因为家属的繁殖,不得不贪婪的去占有土地,又由于劳动力多,全家十六口人,无分男女老幼,都要到地里去,大家征服土地,于是土地的面积,一天天推广,一直到不能不临时雇上一些短工。于是穷下来的人把红契送到他家里去,地主家的败家子在一场赌博之后也要把红契送给他。他先用一张纸包契约,后来换了块布,再后来就做了一个小木匣子[26]。
同样地,丁玲对当甲长发了财的江世荣,私通日本势力致富的大地主钱文贵的角色素描都有类似的笔法,只不过,顽固的剥削阶级钱文贵反对土改,最后被设定为标的处理。丁玲预留剥削阶级“改造”与“自我改造”的空间,诉诸于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转换,才是丁玲叙事的中心命题。
到底谁支持土改?谁被动?谁反对?如何分地?在众多研究中国农村组织、中国合作社历史的资料,较难表达村集体内部喜闻乐见、紧张的阶级张力或社会关系转化的关键点。顾涌的儿媳妇董桂花当上妇联会主任感叹到:“她回忆着去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她是多么辛苦呵!她一家一家的去找,男人们都在骂妇女落后,可是妇女呢,总说‘咱知不到嘛!咱听不精密’。开会的时候,谁也不张口,不出拳头。她也不懂什么,可是不得不站在台阶上喊叫[27]。”董桂花当过扫盲运动识字班组织妇女。她感受到年轻妇女:“只有这些无忧无愁的年轻的媳妇们和姑娘们,欢喜识字班,她们一天来两三个钟头,识三四个字,她们脱出了家庭的羁绊和沈闷,到这热闹地方来,她们彼此交换着一些邻舍的新闻,彼此戏谑,轻松的度过一个春天,而夏天又快完了[28]。”
暖水屯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支部书记张裕民的工作更为艰困,他花许多时间了解地主与富农,组织“土地改革问答”读书会,几位青年在其中获得思想改造,如:“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下去越觉得有兴趣。他常常联系村上的具体人物来说明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应该打击谁,应该照顾谁,愉快的笑不离开他的脸[29]。”后来李昌加入村支部宣传工作。在土改工作组长文采的建议下走“群众路线”,成员包括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村副赵德禄、治安员张正典、民兵队长张正国、工会主任钱文虎、支部组织赵全功还有李昌等八人启动了复杂的土改运动。
稳健的程仁在过程中发现:“他觉得土地的分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问题,要能使全村人满意,全村都觉得是公平的才算把这件事做好了[30]。”他认为:“‘按土地改革,就是分地,只是——’程仁想起了孟家沟的大会,又补充道:‘也要斗争!’[31]年轻气盛的李昌还在追着问:“咱们这次该斗争谁?”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他们脑子里一个一个的去想,有时觉得对象太多,有时又觉得都不够条件,或者他们想到过谁,却有顾忌,他们不好说出来。”[32]
土改八人小组关于土改作法有诸多分歧,其中有许多的争吵,丁玲最后以合题的观点处理了。“总之,大家的思想是否就一致了呢,不一定,大家也并不明白明天该办些什么事,但大家都轻松了好些,他们的情感结在一体了。他们都有一种气概,一种赴汤蹈火的气概[33]。”
在边区政府图书馆工作的土改组组长文采是知识分子,“他在延安住了一年,学习文件,有过很多反省,有些反省也很深刻,并且努力改正了许多不务实际的恶习。他诚心要到群众中去,向老百姓学习。但他去了之后,还是爱发挥些理论,把他那些学问,那些教条,那些道听途说,全搬了出来[34]。”文采来到暖水屯:“参加村的清算工作,一个多月的经历,给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农村是一个大的活的图书馆,他可以读到更实际的书。这些实际的生活,更能启发他和明确他的人生观,以及了解党的政策。尤其使他愿意去的是这里有一种最淳朴的感情,使他的冷静的理智,融会在群众的热烈的浪潮之中,使他感觉到充实和力量。”[35]但是文采含混,难以决策的弱点,让土改工作的进行并非一路顺遂。
暖水屯村民欢迎分地,但是对于斗地主的方案有所保留。比如小地主许有伍有十亩地,“去年已经分给二十家赤穷户。假如这十亩地,可以收获三万斤,那末至少值钱三百万元。每家可分得十五万,合市价价能折小米七百五十斤。三口之家,再拉扯点别的活计,就勉强可以过活了,要是还有一点地当然更好[36]。”分许有伍地,获得小小成果,但是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土改小组继续争吵,“一些纠缠不清的争论,继续着,一些夹七杂八的所谓群众观点,空洞的语言,使胡立功(土改小组成员)不能忍受了,他跳起来说:‘咱们的工作,如果老这样吵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前途,就是垮台!我也曾经做过减租减息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做法!’‘是的,我也认为工作组的意见太难于统一了!’文采慢吞吞的答道,‘枝节太多,民主也太多,很难集中。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对政策理解的深度不一致。不过,至于工作,我想还不至如你所希望──就说是担心也可以──那么的坏吧。哈……’[37]”
在土改工作混沌不明,暂时受到阻碍时,丁玲文学的笔触,转化了读者焦虑与书中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在肃穆的,清凉的果树园子里,便飘起了清朗的笑声。这些人们的欢乐压过了鸟雀的喧噪。一些爱在晨风中飞来飞去的有甲的小虫,不安的四方乱闯。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一累累的沉重的果子。在那树丛里还留得有偶尔闪光的露珠,就像在雾夜中耀眼的星星一样。那些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润湿。云霞升起来了,从那密密的绿叶的缝里透过点点的金色的彩霞,林子中反映出一缕一缕的透明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薄光[38]。
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有工作的急迫性,但是土改干部们所坚持的“群众路线”,讲究:“干部也不只是布置些工作,下命令,要自己也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更懂得一切应该依靠谁,怎样才能从老百姓中找到最可靠的朋友──穷人了!”“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39]。”透过密集的群众大会、民主选举,穷人有了自信。小组如何分地,小说描写的很清楚:
他们决定在旧历八月十日分东西;十四的晚上讨论分地;十五发出地亩条子,并且分卖果子的钱,晚上,全体休息;十六量地去,赶忙量好了地就要收秋了。
十四的那天,分得了领条的,都准备好了搬运东西时所需要的对象。有的准备了绳子,棍子,有的准备了麻袋,邀好了人,妇女也出发了。这次分东西分得很普遍,有许多中农也分到了一个小瓶,或者一个镜子,因此去领对象的人特别多。小组长们也分开了几个地方负责,对条,发货,号码不能错,人名不能错。货物出院还得有新条,有图章戳记,有条有理,一点也不会错。工作组的同志全来了。评地委员会的人也全来了。他们的地已经分好了,已有了空闲,有的人也要来搬取物件[40]。
小说中的素朴的财产重分配的情景,令人惊讶于四十年代的北方地主所拥有的财富却也相对的薄弱,但是几个地主集中起来的对象与土地积累,还是比多数穷人丰富。“人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很多家具,从好几条路,搬运到好几家院子里,分类集中。他们扛着,抬着,吆喝着,笑骂着,他们像孩子们那样互相打闹,有的嘴里还嚼着从别人院子里拿的果干,女人们站在街头看热闹,小孩们跟着跑。东西集中好了,就让人去参观。一家一家的都走去看。女人跟在男人后边,媳妇跟在婆婆后边,女儿跟着娘,娘抱着孩子[41]。”
群众对分配政治得来的成果不易,县宣传部长章品从法治的角度,纠正了以暴制暴的群众情绪发展,他说把地主打死:“这是一种变天思想,咱们要纠正它,随便打死人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搜集他的罪状交给法院,死人不经过法院是不对的。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你得说服大家[42]。”但是,地主钱文贵成为群众千年怨气发泄的对立物,因为:“几千年的恶霸威风,曾经压迫了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在这种力量下一贯是低头的。他们骤然面临着这个势力忽然反剪着手站立在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反倒呆了起来,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有些更是被那种凶狠的眼光慑服了下去,他们又回忆着那种不堪蹂躏只有驯服的生活,他们在急风暴雨之前又踌躇起来了[43]。”
暖水屯的土改运动是成功的,
这次闹土地改革到此时总算有了个眉目,人们虽然还是有许多担心,但总算过了一个大关,把大旗杆拔倒了。他们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同村子上的恶势力打仗,他们还要一个一个的去算账。他们要把身翻透。他们有力量,今天的事实使他们明白他们是有力量的,他们的信心提高了,暖水屯已经不是昨天的暖水屯了,他们在闭会的时候欢呼。雷一样的声音充满了空间。这是一个结束,但也是开始[44]。
许华斌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过一条主线、几条副线的交错发展,几十个人物的刻画,表现了当时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反映了丰富的生活内容,体现出一个重要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45]。”张如法和徐明霞认为此部作品是一部典型的群像体小说[46]。
暖水屯的土改运动的故事,详述了群众与领导干部关系、社会运动智慧与群众能动性外,占百万分之一的暖水屯经验,可谓五十年代的集体化农业带来何种基础?丁玲的五十年代的参与有带来何种反思?纲要的制订与推行如何反映在丁玲小说中所描写的五十年代,如《粮秣主任》《杜晚香》。
丁玲的五十年代与纲要
五十年代的丁玲的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依旧在四十年代的基础行进,1955年9月到12月期间,丁玲到北京西郊海淀区农村采访建立高级合作社的进展情况,并着手写短篇小说《杜秀兰》(未完稿),1954年6月在黄山开始动笔[47]。1956年10月,应邀在四川大学作报告。《在严寒的日子里》前八章在《人民文学》第十期上发表。[48]
1957年7月,丁玲到了汤原农场一分场畜牧队,先后在孵化室,育雏组参加劳动。冬季在饲料室帮助剁菜,并亲自到牡丹江畜牧场买良种鸡,计划做改良鸡种的试验。1959-1964年,丁玲任畜牧队专职文化教员,在任教期间,丁玲担任扫盲班的教学,并主持队上的文娱活动。丁玲所带领的文化风气,在三年困难时期,运用适合群众兴趣的形式,坚持文化学习[49]。
学者任军莉、周佳的《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我国新型农民培养》一文中重新整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对于中国解放后社会主义国家农村战略的布局[50]。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有6亿人口,农民占了5亿,而这5亿农民中文盲和半文盲又占据多数。1953年10月、毛泽东曾提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所以,个体农民必须走合作化道路,培养现代新型农民,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一项系统工程[51]。
制订《纲要(草案)》之前五年,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期(到1952年底),当时已有占全国总农户39.9%的4542万户农民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历经三年的发展,“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内,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梯、三种形式,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尽管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中,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但是,整体来看,这场农业的大变革在当时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52]。”
总体来看,《纲要(草案)》共有四十条,大到合作化制度、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教育,小到具体的肥料使用、农具改造、土壤改良、勤俭持家,对农业发展全面规划。
《纲要(草案)》提出在农村建设的积极层面是,1956年开始,男性劳动力每年至少做250个工作日,积极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和副业生产的劳动,要求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120个工作日。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必须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成立农忙托儿组织。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应当予以照顾。扫盲工作,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扫除文盲的标准是认识1,500字以上。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必须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在乡设立业余文化学校,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分别用7年或者12年时间在各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乡村小学基本上要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理[53]。
《纲要(草案)》培养了农村青年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农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生产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活动分子和突击力量。对于传统的农耕掘提出改造洼地、推广和使用新式农具,培育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防止土地盐碱化、注重水土保持等方法。
从1956年到1967年(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的全国农业发展规模的纲要的草案明载,1955年已经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85%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54]。春季,全中国有2.5亿人口(约五千万户)加入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组织。[55]
从《纲要(草案)》提出到实践,为往后集体经济奠下基础。以浙江为例,李琳琳、朱强、王景新在五个集体经济村做调查,发现这段期间所创立的互助组、互助网、初级社、高级社延续至今为当今浙江农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依然存在的村经济合作社、村股份合作社、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生产/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社等依然活跃于农村生产之中[56]。
完稿于1954年《粮秣主任》和1965年的《杜晚香》两部作品,最能表达丁玲对于五十年代互助合作运动的内涵[57]。《粮秣主任》表现了老共产党员一生无私为集体化道路努力的痕迹,带领着积极富有希望的社会力量。《杜晚香》则描述了翻身后的基层妇女干部学习向上,当“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58]。
《粮秣主任》小说中的官厅村:“是个穷村,连个小地主也没有,真真够得上富农的也没有。村子只有五十来户人家,都是好人,所以八路军没来多久就建立了村政权和发展了党员。李洛英还不是最先加入的。因为环境较好,所以区乡干部下来了就常常住在这里。」解放后,「是的,旧的官厅村,穷苦的,经过了多年斗争的官厅村没有了,压根儿没有了,这里有的是更广阔的,新的,幸逼的世界。湖山变得更美丽,人变得更可爱;粮秣主任艰难的生活过去了,李洛英成为更加有生气的,充实的,懂得生活的水位看管人[59]。”
建国初期,官厅村的农村现代化展开,农村的社会性质有了改变:
远处传来一声最大的震响,大约是燃料工业部炸山炸开了一块较大的地方,我们好像又回到现实世界,我走到门口去看,下游修坝的地方,探照灯,水银灯,照得像白天一样,一片雪亮的光。
她说得倒好,说过几年农村也要工业化的,她不反对工业化,她将来就留在村子上开拖拉机。你听,说得多好听,哼!后来才知道,一人家已经自己找下“对象”了,还不是一个耍土圪塔的。
官厅村一共有二十多个人转了业,都跟着水库的修建转入了工业。都是年轻人,都比我强,他们都不只做工,还学习到技术。那个李洛平一年就学会了掌握车床,如今已经在带徒弟呢[60]!
年轻的水库看管仁李洛英望着官厅村的变化,把寄托之情归于老粮秣主任的领导,他说:“老粮秣主任啊!你在想什么呢?你的艰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你所有的愁苦,斗争,危险和欢欣都同时涌现了出来,都在震动着你的心灵吧。我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想,我不能离开他,我愿意和这个主任同在下去,坐在一道,静静地听着外边的嘈杂,和看着渐渐黑了下去的暂时仍然有些荒野的山影[61]。”
《杜晚香》是小山沟村的劳动妇女,这小村只有二十来户,土改工作复查队进村做了杜晚香工作,把她升为妇女主任。她的爱人李桂从51-54年参加抗美援朝从军去了。五八年李桂退伍,自愿到了北大荒开荒,杜晚香亦勇敢的跟随着他前往。当时北大荒的气息:“被包围在这美丽的天地之间的农场景色,就更是壮观,玉米绿了,麦子黄了,油漆过的鲜红鲜红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宛如舟艇,驰聘在金色的海洋里,劈开麦浪,滚滚前进。它们走过一线,便露出了一片黑色的土地,而金字塔似的草垛,疏疏朗朗一堆堆排列在土地之上。太阳照射在上边,闪着耀眼的金光。汽车一部接着一部在大路上飞驰。场院里,人声鼎沸。高音喇叭播送着雄壮的进行曲和小调,一会光是男低音,一会儿是女高音,各个民族的醉人的旋律,在劳动者之间飘荡。人们好像一会儿站在高山之巅昂首环顾,一会儿浮游在汹涌的海洋,追波逐浪;一会儿又彷佛漫步于小桥流水之间,低徊婉转,但最令人注意的,仍然是场院指挥部的召唤,或是关于生产数量与质量进度的报告[62]。”
有 妇女组织工作经验的杜晚香任劳任怨,又有服务心:“全场院的人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这个个儿不高,身子不壮,沉静地,总是微微笑着的小女子;奇怪她为什么有那么多使不完的劲,奇怪在她长得平平常常的脸上总有那末一股引得人家不得不去注意的一种崇高的、尊严而又纯洁的光辉[63]。”杜晚香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她总是在她遇到的各种各式的人和事物中,显出她宽大的胸怀;她只是悄悄地为这个人、为那个人做些她认为应该做的小事,她总是总是被全体一致地推选是队的又是农场垦区的标兵了。
她捡了公粮交给国家,她照顾大城市来的无知知识青年,“大都是中学毕业生,懂得许多名词,会说会道,能歌能舞,好不天真活泼,十三队来了二十多个这样天之骄子的姑娘,”杜晚香“无微不至地,信心百倍,始终如一,兴致勃勃地照顾她们,引导她们,她打心眼里爱这群姑娘,她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放弃了城市的优裕生活,到艰苦的边疆来学习劳动的,是群有着雄心壮志的幼苗,她应该以爱毛主席、爱党的一颗热心去照顾她们,她觉得自己也还要向她们学习咧[64]。”她们一起替她起草工作计划,整理学习心得,还有各种各样的发言稿,杜晚香经常被邀请出席一些模范工作者的座谈会,要到生产队去讲经验,要参加垦区、省的劳模经验交流会议。
这一切的一切,支持杜晚香的是走向新人的准备:
她从她的幼年讲起,那穷僻的小山沟,那世世代代勤劳苦干、受尽剥削压迫,而又蒙昧无知的人们的艰难岁月;在这落后的受折磨的痛苦生涯中,她是多么幻想过另一个世界,另种生活,和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呵!听的人都跟着杜晚香走进了阴暗而沉重的时代,走进了劳苦人民的心灵。他们回想到自己、回想到被狂风暴雨侵袭鞭打过的祖祖辈辈,回想到祖辈们的坚强的生的意志和斗争的毅力。尽管旧中国的头上曾经压着三座大山,但劳动人民显示了力量,杜晚香就是从无限的干旱的高塬上挤出来,冒出来的一株小草,是在风沙里傲然生长出来的一株红杏[65]。
结论:丁玲的文学资产
丁玲五十年代年后,介入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改造自己,留下众多参与这场历史性的盛会的群像,这些故事不仅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更为九十年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所展开的合作化运动、社会与团结经济带来无穷的社会资产与实践策略,丁玲不仅仅是文学的,也是解放政治的见证者。
因此,当下重读五十年代前后丁玲的文学,启发着三点结论:
(一)中国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源于农民社会的两极分化,合作化与集体化是透过人民战争打斗出来的战果与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农民生产与生活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建立提供了基础,重新建立大范围内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经过改革开放,村集体大部分改变,但仍留下为数不少的集体经济仍腰杆挺立着。然而正如林春所言,中国虽避免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区,城市二元结构也限制城市的过剩资本下乡,但是去集体化的道路让国际市场极度剥削获得超级利润。当今中国,农村:“女性地位的倒退,宗族关系、迷信习俗的复活,家庭分离,老幼无养之苦[66]。”林春提出农业直接生产者若能依靠法定的集体所有制和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是否是社会主义中国挺住的关键?
(二)然而社会科学群体或互助合作运动的倡议者对于“组织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的想象光从田调经验与资料搜集,并不能丰富化其社会内容复杂与细腻的社会关系的建设与改变,文学成为可能,丁玲的五十年代的文学贡献,可将提供往后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反思。
(三)巴黎公社紧紧维持72天,当列宁的苏维埃政权挺过72天,他在73天时跑到雪地上,高兴地叫说苏维埃比巴黎公社多了一天。人类的解放政治是在黑暗中匍匐前进。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阵营,在白色恐怖中奋起的左翼力量几乎被扑灭,六十年代青年造反年代的进步青年一部份人到了山区“从上井冈山”或重建公社。“丰饶的公社”(Communal Luxury)一书作者克里斯汀·罗丝(Kristin Ross)就认为不管是用庆贺或者批判的态度来谈公社的成功或失败,最重要的是这些公社的经验是否可以提供未来革命的教训[67]?
(作者系台湾成功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韦护》丁玲著;台中市:文听阁, 2010。
2. 《丁玲》丁玲著;杨桂欣编;台北市:书林,民81。
3. 《丁玲研究 = Studies in Ding Ling》中国丁玲研究会编;湖南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发行:新华经销,1992。
4. 《丁玲小说研究》许华斌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新华发行,1990。
5. 《丁玲散文》丁玲著;范桥,卢今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新华经销,1997。
6. 《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邢小群著;台北市: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红蚂蚁经销,2009。
7. 《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丁淑芳著;范宝慈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8. 《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丁言昭编著;台北市:业强,1998。
9.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丁玲的最后生涯(1949-1986)》秦林芳著;台北市: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红蚂蚁经销, 2008。
10. 《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丁玲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新华发行,1989。
11. 《丁玲创作论》;邹午蓉著;南京市:江苏教育出版:新华发行,1994。
12. 《丁玲全集》第二册与第四册,丁玲著;张炯主编;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经销,2001。
13. 王景新《村域集体:史与展》,中社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五章 中共早期的互合作及其制度探索》,第143-176。
14. 朱为群,《中国三农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15. 程同顺:《中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16. 张慧鹏:《中国农业是如何走上石油化工道路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体制机制动力》,《开放时代》2016.03总第267期,广州:开放时代杂志社,2016,页176~189。
17. 林春,《小农经济派与阶级分析派的分歧与共识:“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评论》,《开放时代》2015.5,总第263期,125-129。
18. 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型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06总第264期,广州:开放时代杂志社,2015,页53-81。
19. 任军莉、周佳的:(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我国新型农民培养),《现代哲学》,2016.09总第148期,页50-55。
20. 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1. 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载。
22. 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3.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研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2002。
24. Eric R.Wolf,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1,Faber andFaber,3 Queen Square, London。
25. William Hinto,1966,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Chinese Village,Ving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New York。
26.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Paris Commune London:Verso,2015。
27.http://www.cwzg.cn/theory/201703/34688.html。
注 释:
[1] 服务于台湾成功大学台文系,副教授,本文酝酿于广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2016年12月3日)特别感谢广州大学副校长俊忠教授的启发,与浙江大学王景新教授的观点。感谢我的助理钟恬安的协助。
[2] 王景新《村域集体:史与展》,中社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五章 中共早期的互助合作及其制度探索》,第143-176。
[3] 同上。王景新提出:“中央苏区土地全部之80%集中于地主富农手里(祠堂寺庙富农也在内),尤其是肥沃的土地是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有。但人口的阶级比例则以贫农为最多,占全人口70%以上。土地垄断致使地租剥削严重,寻邬的田租一般占全部收获量的50%至56%,兴国少数为50%,大多高达60%到70%;闽西更剧,田租最低是60%,长汀70%,连城南乡高至80%。”
[4] 不同于苏联所经验的“战时共产主义”(1918-1920)或一战之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919-1939)经验,中国苏区经验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北京大学的谢有实认为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战争期间客观现实的动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动员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力,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谢有实,「“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世界历史,1981年第1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受制于右翼政党与法西斯运动的挟击,而苏联激进的革命经验又难以复制,因此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难以维系。见http://science.jrank.org/pages/11297/Socialism-Socialism-in-Interwar-Period-1919-1939.html#ixzz4bARW2T00
[5] 同上。董必武于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的《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1917﹒8﹒27)报告提起土地改革的效力,但是生产工具、技术与组织力的落后,成为讨论的重点。王景新:互助合作组织已经发展到多种领域,如解決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缺乏而成立的耕田队,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保障军需民用而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便利群众生活而成立的消费合作社,平抑苏区粮价而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抵制高利贷盘剥而成立的消费合作社等;互助合作內容已经由劳动力互助、畜役和生产工具互济,发展到合作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融资和发展农工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內部治理結结构基本形成,社员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审查委员及其下設生产、发卖、采办、保管、会计筹股室等办事机构一并俱全;互助合作组织內部的分配决算制度也已经成型,而符合国际合作组织通行规则,比如按照股份和惠顾额分红,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充裕发展资本,奖励有功成员,处罚犯错误的领头人等等。
[6] 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型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06总第264期,广州:开发时代杂志社,2015,页53-81。
[7] 同上。王教授指出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面队三大难题:1.日帝侵华,冀中、太行山等根据地损失惨重。2.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费,对边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3.自然灾害严重,如太行区和冀中平原,灾人口达到50%以上,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8] Eric R.Wolf,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1,Faber andFaber,3 Queen Square, London,书中提起的新农村组织如village councils,work teams,peasant unions。
[9] 同上,页150。
[10] 同上,页154-155。
[11] William Hinto,1966,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Chinese Village,Ving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New York,页7,原文: Thus didthe war grow in ferocity and ruthlessness. As both sides girded forincreasingly decisive battle the possibility of compromise receded swiftly intothe background. Each day brought new evidence that 1947 would be a year ofdecision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12] 同上,页7。
[13] 朱为群,《中国三农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14] 同上。
[15] 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页1。李松睿借用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和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说法。
[16] 贺桂梅:《知识份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摘。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4。
[17]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2002。
[18]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 丁玲与延安作家的身份冲突》,贺梅:《女性文学与性別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9。
[19] 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台北市:秀威资讯科技出版 : 红蚂蚁经销,2009,页59。
[20] Freedictionary,http://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Criticism+and+Self-Criticism
马克思提起“批判的武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的状态下,批判是无产阶级有效的武器。列宁强调批判与自我批判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的核心。当社会主义消除了剥削阶级与矛盾时,批判的日的与本质会转化,旧系统的解体与革命性的推翻武器成为工具,批判会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创造提供动力。
[21]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在1946年参加河北省怀來、涿鹿、获鹿等县土地改革的成果。见姚锡佩《丁玲及其创作的世界意义》,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研究》,湖南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发行 : 新华经销,1992,页155。
[22] 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新华发行,1990,页173~174。
[23] 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新华发行,1990,页174。
[24] 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新华发行,1990,页176。
[25] 叶昌前《论丁玲的文体风格》,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研究》,湖南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发行 : 新华经销,1992,页373。
[26] 《丁玲全集第二册》丁玲著:张炯主编;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经销, 2001,页9。
[27] 同上,页29。
[28] 同上,页30。
[29] 同上,页42。
[30] 同上,页43,47。
[31] 同上,页52。
[32] 同上,页53。
[33] 同上,页56。
[34] 同上,页69。
[35] 同上,页58。
[36] 同上,页113。
[37] 同上,页178。
[38] 同上,页185。
[39] 同上,页211,218,245,247,252。
[40] 同上,页297。
[41] 同上,页295。
[42] 同上,页253-54。
[43] 同上,页267-268。
[44] 同上,页274-275。
[45] 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新华发行,1990,页181。
[46] 张如法 徐明霞《丁玲的群像体小说》,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研究》,湖南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发行:新华经销,1992,页377。
[47] 《下卷 牛棚小品》:附录三:《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丁玲:《魍魎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新华发行,1989,页285。
[48] 同注3。页286。
[49] 《下卷 牛棚小品》:附录三:《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九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丁玲:《魍魎世界 风雪人间:丁玲的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新华发行,1989,页287-288。
[50] 任军莉、周佳的:(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与我国新型农民培养),《现代哲学》,2016.09总第148期,页50-55。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同上。
[54] 同上。
[55] 程同顺:《中国农民组织化研究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6] 李琳琳、朱强、王景新,浙江农业合作化名村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发表于广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2016,12.3)。
[57] 《丁玲全集》第四册,丁玲著;张炯主编;石家庄市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经销, 2001,页275-288。
[58] 同上,页289-313。
[59] 《丁玲全集》第四册,丁玲着;张炯主编;石家庄市: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经销, 2001,页275-288。
[60] 同上。
[61] 同上。
[62] 《丁玲全集》第四册,丁玲著;张炯主编;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经销, 2001,页289-313。
[63] 同上。
[64] 同上。
[65] 同上。
[66] 林春,《小农经济派与阶级分析派的分歧与共识:“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评论》,《开放时代》2015.5,总第263期,125-129。
[67]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Paris Commune London:Verso,2015。